 参加活动: 0 次 参加活动: 0 次
 组织活动: 0 次 组织活动: 0 次
- 鲜花
- 25
- 鸡蛋
- 0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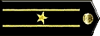
陆军少校
|
本帖最后由 蚌论樱桃 于 2018-12-21 08:30 编辑
B:蚌埠话、大麻虾、花鼓灯、烧饼夹里脊…… A:还有别的吗?比如说冬天的? B:穿睡衣上街? A:emmmmm......
作为一个纯正蚌埠人,听到这样的回答,我的内心是奔溃的。老铁,你们对蚌埠了解太少了!尤其在冬季的时候,更是对蚌埠人一无所知。冬季的时候,蚌埠人尤为喜爱泡澡。喜欢南方人洗澡大多也就冲一冲,像广东人就把洗澡叫“冲凉”。
但是在蚌埠,冬天洗澡,我们是认真的。
“一周必在外面洗一次,在家洗的不算洗”的洗澡观念根深蒂固地盘踞在每个老蚌埠人的心中,而且每次在洗澡上耗费的时间,很少会低于一个小时。对蚌埠人来说,在外面好好洗个澡的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一饭一蔬。
不同于南方地区的单独浴室,蚌埠人的公共浴室风格更偏北方。在蚌埠,这种浴室俗称大澡堂子:水泥地、白瓷砖、木质躺椅,还有那块热气腾腾的“水池子”,掀开棉制门帘一进大厅,马上就会觉得由寒冷冬天进入了一个暖洋洋的世界。这一切的情形,构成我们对于老澡堂最初的印象。
在过去,人们下了班后,往往泡一壶茶,约几个“澡友”,泡几个小时“软水”,坦诚相对,聊天会友,谈天说地,很解乏。敲个背、修个脚、拔个火罐,躺在木椅上一边喝茶一边和熟悉的澡友或者澡堂师傅吹吹牛。没有豪华的装修,简朴中透着亲切和周到,在这里讲究的就是人气和人情。
澡堂的顾客以中老年人为主,大多是熟客,和澡堂老板关系很要好。顾客付了钱,澡堂的伙计就会递上一把牌子,顾客拿了牌子就下池子去泡几个小时的“软水”。这牌子上有个标号还绑着钥匙,方便搓澡师傅认人。
洗澡讲究在泡,先在淋浴冲一会,然后赤条条沉入大池子中,等你把身上泡舒服了,搓澡师傅就会让你在池边或坐或躺,用一条搓澡巾帮你搓得全身通红,污垢去得干干净净。现在的小朋友们基本不会选择搓澡,一方面是因为要另外收费,另一方面是因为搓起来还是很有些疼的。而且小孩没那么多老泥,往往不需要搓,最多家长给打打肥皂了事。
需要注意的是,大池里面是不允许冲肥皂沫的,也正因为如此池水水质看上去可以让人接受。但讲究的人还是要洗上午八点钟开门的头把澡,那水一定是当天新放入的,不像晚上十点钟的大池,那真是一锅“混沌汤”。
擦干身子后,人们都会泡杯茶在躺椅上歇会儿,享受老师傅的修脚、按摩服务。浴客间操起各地方言,彼此之间谈天说地,无比热闹。小编记得以前常去的华清池澡堂有个服务员是个足球迷,每次去他都和一些相熟的澡客狂聊足球,我们就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。
看到这,可能有小伙伴们会问,地处南北分界线的蚌埠,为什么冬天洗澡泡澡的风俗更接近北方,而不是流行南方的单独浴室?!
其实这得从气候和经济说起:最初蚌埠人一起洗澡,主要还是因为冷,以及穷。
相比南方冬季温暖湿润,北方的集中供暖,蚌埠的冬天显得较为湿冷,1月最低温平均值为-4°C左右,有时间还会跌到-10℃。三九天,寒风吹到身上,刺骨的冷,冻得浑身哆嗦。
此前,家家户户只能自己烧蜂窝煤或小锅炉取暖、做饭、生活。且不说乌烟瘴气、异味呛人,小炉子的实际取暖效果非常有限,毛衣棉袄一件都不能少,脱个精光洗澡更不可能。而热水的唯一来源就是小炉子上的铁皮水壶,即烧即洗也只能勉强够用。
冬季洗澡对水温和室温的需求促成了公共浴室的繁荣。澡堂店主用大锅炉烧热水,铺设管道和暖气片,提供了普通人家里无法创造的洗浴条件。市场经济之前,大澡堂基本上都是国营的,票价不高,城市里国营浴室的数量也不会太多,冬天基本上每天都人满为患。
受限于物质经济条件,无法在每个单间里都安暖气片,所以索性就敞开了,铺一组大的暖气片给一整间澡堂供暖。被冻到质壁分离的蚌埠人,迫于无奈只好把隐私二字抛在脑后,没有隔间的大澡堂子就这样流传了下来。
倘若在国营工厂或事业单位工作,则无需和陌生人在大澡堂里推推搡搡。改革开放前期,蚌埠是著名的老工业基地,各种化工厂、钢铁厂,工人们住的是工厂家属院,吃的是工厂食堂,逢年过节拿的是工厂的油米肉酒,工厂烧锅炉余下了很多热量就造个大澡堂烧热水。来洗澡的人们既是同事也是街坊邻居,难得不用奔波于工作和生活,一边泡在热水里一边闲言碎语家长里短,于是洗澡这一活动也被赋予了社交属性。
如今,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家家都装上了热水器浴霸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喜欢冬天在家洗澡。而那些匿藏于街头巷尾的老澡堂要么面临休业关门,要么就升级改造。越来越多的高档洗浴中心拔地而起,人均消费60到无上限。在这种场所,洗澡汗蒸啥的都只是基础,顺带着还可以在里面吃个自助餐,来个SPA,按个摩,唱个K,打个麻将,健个身,看个电影。
一座城市,总有那么一些记忆埋藏在深处。
老式澡堂、古老建筑、风俗习惯……这些,就是城市记忆深处的一张张珍贵底片。有些已不复存在,只能从底片中一窥曾经的风采,而有些,也许换了一种形式继续陪伴着我们。
|
|